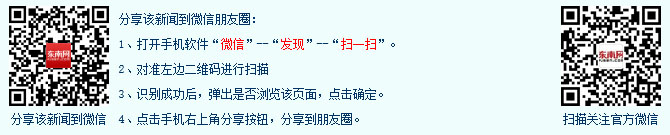|
萬里茶道起點赤石的老時光。張棟華/ 圖 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簽訂后,英國植物學家福瓊(Robert Fortune)受英國皇家園藝學會的派遣,來到中國從事植物采集,將大量中國植物資源送至英國。1848年,福瓊又接受東印度公司的派遣,深入中國內陸茶鄉,將中國茶樹品種與制茶工藝引進東印度公司開設在喜馬拉雅山麓的茶園,結束了中國茶對世界茶葉市場的壟斷,給中國經濟帶來巨大影響。福瓊是科學家,又有特殊任務在身,因此對中國的觀察和認識有獨到之處。他對中國農業水平的判斷、對中國傳統宗教、信仰的看法,都與此前的傳教士和普通外國商人不同。 “茶葉大盜”羅伯特·福瓊盛產茶葉的武夷山等到我完全走出崇安縣的郊區,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大名鼎鼎的武夷山。它包括好些個小山頭,每個山頭看上去都不到1000英尺高。它們外形一致,山上幾乎全是一些陡峭的懸崖。似乎是老天爺某次威力巨大的震動把整個山體抬升到一定的高度,然后另一股力量又把山頭拉得有些錯位,并把這大山頭分裂成上千座小山頭。只有通過這樣的手段,武夷山才有可能呈現出現在這種風貌。中國人把武夷山看作是最為奇特,也最為神圣的地方之一。在鮑爾先生引用的一本中文書里寫道:“在福建省所有的山嶺中,最美當屬武夷山,最好的水也在武夷山。武夷山非常高,也很崎嶇,山環水繞的,似乎有神靈看護,再沒有比這兒更神奇的了。從秦漢到現在,很多方士和修道之人——佛、道兩家都有,都在這兒得道成仙,白日飛升的不可勝數。但武夷山最有名的還是這兒的特產,也就是著名的茶葉。” 在崇安縣到武夷山的半道上,我在一塊隆起的坡地上站了好一會兒,仔細打量著我面前的這一奇特景象。在我還沒到達武夷山之前,我期待著能看到一幅奇妙的風景,我必須承認,眼前的風景遠遠超過我此前所有的想象。那些耶穌會士的描述、那些中國人的著作,除了有關山的高度之外,其他方面一點也沒有過甚其辭。這些山頭并不是很高,實際上,與這一地區的大多數山脈相比,武夷山都要低一些,尤其是和我不久前剛剛翻越的高山比起來,它更是要低得多。隨行的中國人非常自豪地指著那個地方說:“看,那就是武夷山,你們國家有什么山比得上它嗎?” 這一天天氣很好,陽光非常強烈,我只好躲到路邊一棵大樟樹亭亭如蓋的樹冠下面。我本來想一直呆在那兒,直到天黑了什么風景都看不到了再說,但我的轎夫們,眼看著此行的終點就要到了,說他們已經好了,可以上路了,于是我們繼續前行。從崇安縣到武夷山只有四五十里,但這只是走到山腳下的距離,而我們打算投宿的那家寺廟卻在山頂附近,所以我們要走的路程遠不止這個數。到了山腳以后,我們打聽前往寺廟的道路。“你們想去哪家廟?”我們聽到的是這樣的回答,“武夷山上有將近一千家寺廟呢。”辛虎(“我”的中國仆人)解釋道,我們不知道那些寺廟的名字,我們希望到最大的那家去。最終,有人給我們指示方向,前往某處懸崖腳下。等我們到了這個地方,我以為可以在山上半山腰的某處看到寺廟,但我們什么也沒見到,只看到一條在巖石間辟出的小小山路,通向某處似乎難以逾越的地方。我現在必須下轎了,然后在山路上蹣跚爬行,經常要手腳并用。好幾次,轎夫們都停下來不肯走,說轎子一步也前進不了了。但在我的逼迫下,他們也只好跟在我后面爬著把轎子抬了上來。 武夷山茶園關心茶事勝過佛事的和尚此時是下午兩點左右,天空幾乎一絲云彩都沒有,天氣熱得讓人覺得可怕。我沿著這些陡峭崎嶇的山路往上爬,汗水從每一個毛孔中涌出來,我開始擔心要發熱病和瘧疾,以及所有那些旅行者在這種酷熱氣候中容易染上的病。最終我們爬到了山頂,看到一個林木繁盛的地方,我的眼睛為之一亮,馬上知道寺廟就在附近了。我們正在走近的這座寺廟,或者說這一建筑群,坐落在武夷山頂一個小山谷的斜坡上,這個小山谷似乎就是為了建寺廟而特意挖出來的。在建有寺廟的這一側,有一些奇特而又引人注目的巖石,像巨大的紀念碑那樣豎立在那兒。它們彼此之間離得很近,每塊巖石都有80到100英尺那么高。毫無疑問,和尚們當初選址在這兒建造寺廟,就是被這些外表古怪的巖石吸住了吧。方丈和尚的僧房就建在其中一塊大巖石腳下,我們現在就朝那個方向拐了過去。爬上一段臺階,又穿過一道大門,我們來到了寺廟前。一個正在門廊下面玩的小男孩,看到我們立刻跑去通知方丈,說有陌生人看他來了。很快,方丈走了出來,很有禮貌地和我見面。辛虎(作者的中國仆人——編者注)向他解釋說,盡管我來自一個遙遠的國家,但武夷山的美名也傳播到了那兒,所以我決定在武夷山住上一兩天,希望廟里邊能夠在我們停留期間給我們提供飲食和住宿。 1857年福瓊在英國出版《1853-1856第三次中國冒險之旅》一書中的插圖方丈和尚一邊聽著辛虎的解釋,一邊從煙葉袋里掏出一些煙葉來,用手指和大拇指卷成一根煙卷,然后把它遞給我,讓我塞到自己的煙管里。對于住在山里面的人來說,這是一個很尋常的動作,我想,這個舉動表明他歡迎我的到來,帶有很明顯的友善意味。我也同樣友善地把煙卷接過來,點燃煙管,開始抽起煙來。與此同時,我們這位主人把我領進一間最好的房間,示意我坐下,然后他把小男孩叫進來,吩咐他給我們端來一些茶。現在我就在這原產地的山上,品嘗著這純正無任何雜質的茶水。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想喝茶,也從來不像現在這樣如此感激有人給我端茶。在火辣辣的太陽下爬上山來,我覺得又熱又渴又累。茶水很解渴,我的精力很快又恢復了,我想起了一位中國作者說過的話,他說:“茶之為用多矣,種茶,其效日增,飲茶,令人神清氣爽。”(譯者按:福瓊引用的這句話當是從鮑爾《茶葉的栽培與加工》一書中輾轉而來。原文應當出自元代王禎《農書 百谷譜之十》,其文曰:“夫茶靈草也,種之則利博,飲之則神清。”)盡管我已經能在中國的好些地區使用漢語與人交流,但我覺得還是謹慎一些為好,不要在廟里與這些和尚們長時間攀談。我讓仆人去與他們交涉剩下來的一些事情,仆人很能干,可以把我們的事情都交待清楚。他告訴和尚們,我來自于長城以北一個遙遠的國家,不會講這兒的方言。我前面提到過的那個小男孩又來了,他通知我們晚飯已經準備好了。老和尚朝我鞠了一躬,請我前往吃晚飯的餐室。我也不失禮貌地請他走在前面,他當然不肯這樣做,而是跟在我后面,并請我坐在他左手邊的尊位上。桌子上還坐了另外三位和尚,其中一位的相貌讓人看了很不舒服,他的前額很低,一雙眼睛放肆無禮地到處亂看,身上留下了很多出天花的痕跡。總之,他是那種讓人見了就想躲開,不想與其有任何瓜葛的人。年紀大的那位高僧,容貌正好與其屬下相反,他六十歲左右,看上去很智慧,在他的臉上,可以看出溫和、誠實、守信等品格,讓人肅然起敬。我們都在桌邊坐下,每人倒了一杯酒,老和尚說道“呷酒,呷酒(譯者按:原文Chesue, 呷酒 的諧音)”,也就是喝酒、喝酒的意思。每個人都舉起自己的酒杯,和別人碰杯。碰杯的時候,我們互相鞠躬,同時還要說:“呷酒,呷酒。”然后拿起我們面前的筷子,晚餐這才開始。桌上擺滿了小碟子,每個小碟子里都盛著一種不同的食物。我吃驚地發現其中有道菜竟然是小魚,因為我一直以為佛教信徒是不能碰任何葷腥的。其他碟子里都是一些蔬菜,包括竹筍、各種白菜如新鮮白菜和腌白菜、白蘿卜、豆子、豌豆以及其他種種,做得都非常可口。除此以外,還有一種蘑菇之類的菌子,非常好吃。有些蔬菜做得讓人很難相信它們真的是蔬菜。所有的菜,除了前面提到的那盤魚以外,都那么好吃。每人面前還放了一碗米飯,這是我們晚餐的主食。吃飯的時候,和尚們都一直勸我多吃一些。他們推薦哪道菜的時候,就指向那道菜,同時嘴里還要說“吃魚、吃白菜”或者“吃飯”之類的。對我來說,他們的客氣——恕我直言——有些太過火了。因為他們不光是指著那道他們推薦我吃的菜,而且還伸出他們自己的筷子,替我夾菜。這讓人感覺很不舒服,但我還是像他們希望的那樣把這些菜都吃下去了,就這樣,我們成了好朋友。吃飯的時候,辛虎與和尚們進行了一場有趣的談話。辛虎這些年走南闖北,他給他們講了很多有關南、北各個省份的情況,和尚們對此則所知甚少,甚至是一無所知。他告訴他們他去過北京,描述皇帝長什么樣,他驕傲地把自己穿的侍從制服指給他們看。這制服一下子就讓和尚們覺得辛虎是個很了不起的大人物。他們無所忌憚地評論著各省的人,就好像在談論別的國家的人,如同我們英國人談論法國人、荷蘭人或丹麥人一樣。他們不喜歡廣東人,滿洲人不錯——皇帝就是滿洲人,所有的外國人都很壞,特別是鬼子——鬼子指鬼的兒子,他們用這個詞來指代西方國家的人。吃完飯,我們都從桌邊起身,回到大廳。每人面前這時都擺著一盆熱水和一條濕毛巾,好讓我們餐后可以擦把臉。不管夏天還是冬天,中國人都喜歡用熱水洗臉,但他們很少用肥皂或類似的東西。按照這種真正的中國方式擦過臉和手后,我告訴他們我想出去走走,考察一下附近的山嶺和寺廟。我讓辛虎陪著我一起去,我們走下臺階,然后沿著下到谷底小湖的小徑往下走。一路上我們參觀了好幾個寺廟,但看起來都不怎么樣,沒一座趕得上福州府附近的鼓山寺。實際上,這兒的和尚們看上去更關心種植茶樹和加工茶葉,而不是他們的佛事。我注意到,寺廟前面到處都搭著一些竹架子,架子上放著篩子,這些篩子都是用來晾曬茶葉的。和尚們和他們的仆人們都忙著加工這些昂貴的茶葉呢。 1857年福瓊在英國出版《1853-1856第三次中國冒險之旅》一書中的插圖考察巖石和土壤我們走到湖邊,湖水很美。蓮花的大葉子亭亭地長在水面上,水下有金魚和銀魚在游來游去,周圍則都是一些崇高偉岸的山嶺。離開小湖,我們繼續沿著似乎通到某處懸崖下的小徑往前走。遠遠地看上去,這個山谷似乎沒有出口,但走近了才發現那些巨大的巖石之間還是有一道裂口,裂口間有一條小溪流淌,溪邊有一條小路。小溪只有六到八英尺寬,看上去像是日積月累才將巖石沖開,從巖石間擠出這么一條出路來一樣。這些巖石中含有一些黏板巖,它們以巖脈的形式嵌在大塊大塊的石英巖中,而花崗巖則橫七豎八地嵌在這些黏板巖中。這些花崗巖,因為含有青黑色的云母的緣故,呈一種深黑色。在這一地區,很多主峰的峰頂都是由這種花崗巖組成。黏板巖上面是一些砂礫巖,砂礫巖主要由嶙峋的石英石組成,這些石英石由石灰凝聚在一起。與砂礫巖間雜的還有一種石灰質砂巖,在這種石灰質砂巖中,含有白云石灰巖。地質學家現在可以看出來了,武夷山這些大巖石由一種很奇特的混合物構成,這就是他們得出的結論。我從這些巖石上取了一些樣本,把它們帶給了加爾各答的法爾康內博士和薩哈蘭普爾(譯者按:原文Saharunpore,今名Saharanpur, 印度北部的一個城市。)的詹姆森博士,他們兩人都是非常優秀的地質學家。茶田的泥土由一種棕黃色的粘土組成。如果仔細分析這種粘土的話,會發現它由巖石顆粒和腐殖質組成,其中,腐殖質所占比重又相當高,而腐殖質非常有營養,所以種在這種泥土中的茶樹就能茁壯成長。從巖石裂口中穿過去的時候,兩邊都是壁立的巖石,上面還有滴落的泉水。出來以后我們就來到一片空曠的原野。在考察過這兒的巖石與土壤之后,我想看看周遭的風景如何,于是我努力攀上了寺廟旁邊的山頂,山頂視野非常好,不枉我辛苦一場。在我腳下以及四方都是武夷山嶙峋的山石,山谷中、山坡上有很多小塊的肥沃土地,上面都種著茶樹。我站在一個最高的山頭,崇安縣城和星村鎮所在的肥沃山谷都在我眼前一覽無余。縱目遠眺,連綿不絕的武夷山脈從東邊一直延伸到視線之外的西邊,在福建和富饒、人煙稠密的江西之間形成了一道不可穿越的屏障。 1857年福瓊在英國出版《1853-1856第三次中國冒險之旅》一書中的插圖關于猴子采茶的傳說山里的所有土地看起來都屬于這些出家之人,如前所述,他們分屬于佛、道兩派,但相當大一部分土地還是屬于和尚們。也有一些專為供應北京皇室而建立的莊園,它們叫做皇家苑囿,但我估計,這些苑囿在一定程度上還是要接受和尚、道士們的控制和管理。到處都種著茶樹,哪怕是最為人跡罕至的地方,比如峰頂和險峻的巖坡邊緣,也是如此。鮑爾先生曾描述說,據說到這些地方去采茶的時候要用鏈子把采茶人綁起來。我甚至聽人說——我忘了是聽中國人還是別的什么人說的——采茶的時候要請猴子來幫忙,具體是這樣做的:這些猴子似乎不喜歡干這活,所以并不肯主動采茶,如果看到這些猴子到了種有茶樹的巖石上,中國人就朝它們扔石塊,這使得猴子們很生氣,它們于是開始折斷茶樹的樹枝,把樹枝朝著襲擊它們的人扔下來。我不能斷定說,根本就沒有什么茶葉的采摘需要用到鏈子或猴子,但我想,即使有這種情況,那么通過這兩種途徑采來的茶葉數量也一定非常少。絕大部分茶樹還是長在山坡上較為平坦的土地上,這些土地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因為各種腐殖質和高處隨流水沖下來的沉積物變得很富饒了。只有很少一部分茶樹看起來是種植在山間較為荒涼的土地上,這樣的土地在武夷山到處都是。一整天都在山里辛苦跋涉,我累得很早就上床休息了。辛虎后來告訴我,他一晚上都沒合眼。看起來他不喜歡那個面相丑惡的和尚,對福建人也有很強的偏見,他以為這些人會對我們進行謀財害命的勾當。我倒沒有這些擔心,睡得很踏實,直到天亮才醒,醒來以后覺得精力又恢復過來了,可以應付一天的勞累。我叫人送來一些水,美美地洗漱了一番,一天之中只有這時候我才能有這種奢侈享受。在我住在山上期間,我碰到了很多來自崇安縣的茶葉商人,他們來到山上,從和尚們手中購買茶葉。這些人就借宿在廟里,有時甚至是住在附設的僧房里,直到他們的買賣做成了。然后他們把搬運工叫來,把茶葉運到崇安縣去,在那兒,這些茶葉再做一些加工,然后包裝賣往國外市場。第三天早上,因為已經把這一帶山里比較有趣的地方都看過了,我決定換個地方借宿。吃完早飯,我送給老和尚一件禮物,感謝他的好心招待,禮物雖小,但這讓他對我的尊敬增加了不少。我們把轎夫叫了過來,然后離開了舒適的佛寺,往更遠的山里面前進。下一步是到哪兒借宿呢?我心里一點底也沒有。廟里的和尚把我送到大門口,用中國的方式和我道了別。當我們在山里鉆來鉆去的時候,我看到采茶的人們正在山坡上的茶園里忙著采茶,他們似乎正在進行一場快樂而又心滿意足的比賽,互相開著玩笑,到處都充滿快樂的笑聲,還有一些人在唱歌,就像廟里那些古樹上的鳥兒一樣高興。 ? |